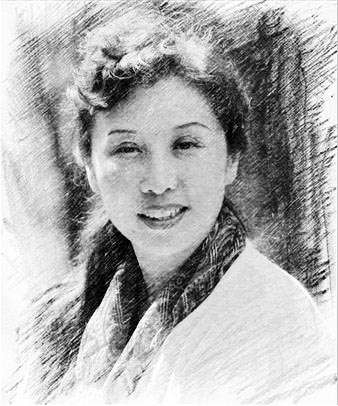
我对巴黎的印象,最初来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唯一传世的自传《流动的圣节》。
海明威对年轻时在巴黎居住的7年有着美好的回忆。他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在巴黎,饥饿和清苦伴随他孜孜不倦的写作,海明威创作并出版了他最早的几部小说。同样也是在巴黎,海明威结识了格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一大批旅欧作家和艺术家,与他们成为朋友。在40年之后,晚年的海明威回忆起在巴黎生活的时光和知交故友,写下了《流动的圣节》,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得以出版。海明威以酣畅的文笔,描绘了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及内心感受。
“一家明亮而干净的咖啡馆,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春天的塞纳河和在饥饿中的创作……”海明威与巴黎那份难以割舍的情缘,始终萦绕其中。
我在不同的章节中,领略到了作者将散文、小说、特写以及创作经验等诸多文体熔于一炉时,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智慧之光。对于这段美好的黄金般岁月,我完全可想象海明威对巴黎的迷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以《明星日报》驻欧记者身份派驻巴黎,年仅22岁。当时他生活穷困潦倒,整日流连在附近的咖啡馆里,位于蒙帕纳斯大道71号的丁香小花园咖啡馆,是海明威最喜欢的光顾之地,他常常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就在这里写作,使得这间咖啡馆乃至巴黎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都充满了浓郁的文学气息。
许多时候,当我想起巴黎,常常会想到“左岸”。在巴黎,以塞纳河为界,河右岸是辉煌的卢浮宫,幽雅的香榭丽舍大道,经典的大歌剧院,是巴黎最为华丽的风景;而在河对面的左岸,是密密麻麻的小巷,拉丁区的大学。许多生活拮据的艺术家和大学生在此流连忘返,使这里逐渐成为各种新潮思想的发源地。左岸的咖啡馆因此也成了具有精神勇者和前卫思想人士追梦驻足的地方。
在我心中,300多年来,左岸的咖啡不仅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和一份文化关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符号象征、一个时髦的词语。难怪我的法国好友墨乔说,当你随便走进巴黎的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思考时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时用过的台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前。
海明威写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内容几乎全都是描写他年轻时在巴黎的际遇。后来,他的《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左岸的几家咖啡馆也因为海明威而在世界享誉盛名。
在历史上,不少法国的政治家是一手端咖啡杯,一手治理天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是一个咖啡迷;拿破仑一生喜爱咖啡;法国杰出的外交家塔列兰曾经说过:“最理想的咖啡,纯洁得像天使,甜蜜得像爱情。”大文豪巴尔扎克没有咖啡就不能工作,他无论去何处写作,除了纸和笔之外,总是把咖啡壶作为第三件必备用品……
来到时尚之都巴黎,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有着醒目汉字“双叟”雕刻的双叟咖啡馆,就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曾经因许多著名作家如海明威、王尔德、乔伊斯、萨特等的光顾,而成为巴黎最时尚的咖啡馆,对于提高巴黎城市知名度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弗罗尔咖啡馆的名声,不知何时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法国咖啡馆时尚的标志。法国人喝咖啡似乎不在于味道,而讲究的是环境和情调,慢慢品,细细尝,读书看报,高谈阔论,一喝就是大半天。
为此,我不止一次地与法国朋友交流,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挥霍时间,法国人更愿意相信,人类深邃的哲学思想、灿烂的智慧火花、独特的艺术灵感,似乎都是在这宽松和谐、富有诗意的氛围中奇思妙想,迸发出来。
法国人养成这种喝咖啡的习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一种自信优雅和浪漫,营造生活的氛围和情调。在我看来,这就是法国传统独特的咖啡文化。
美国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他的《巴黎到月亮》一书中,对巴黎的咖啡馆有着生动的细节描写:“世纪末的法国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记录着很多小事,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似乎主要是在说,什么东西使巴黎仍然是巴黎。”我想,咖啡馆就是“使巴黎仍然是巴黎”。
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相互交流文化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与国度,需要在文化间沟通心灵。
在我眼中,法国文化的特色,则是从众多难以忘怀的小事中,凸显出独特的魅力:时装、香水、法国餐;巴黎、咖啡、海明威……







